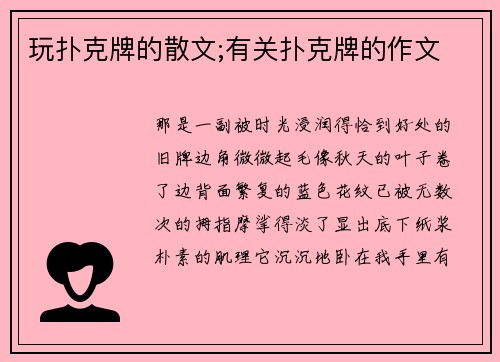玩扑克牌的散文;有关扑克牌的作文
那是一副被时光浸润得恰到好处的旧牌。边角微微起毛,像秋天的叶子卷了边;背面繁复的蓝色花纹,已被无数次的拇指摩挲得淡了,显出底下纸浆朴素的肌理。它沉沉地卧在我手里,有生命的重量。洗牌时,那声音不是新牌脆生生的“哗啦”,而是温存的、絮语般的“沙沙”,仿佛在诉说它所见证过的所有黄昏与夜晚。
我总疑心,每副牌都有自己的性格。这一副,想必是温和而宽容的,因为它总出现在外婆家那张掉光了漆的红木方桌上,陪着我的长辈们消磨了数不清的闲散光阴。那时我还小,够不着桌面,便跪在冰凉的长条板凳上,下巴颏儿勉强搁在桌沿,看他们打一种叫做“升级”的、节奏缓慢的牌戏。他们说话的声音是轻缓的,出牌的动作也是徐缓的。外婆用她那布满老年斑的、枯瘦的手,慎重地抽出一张梅花K,轻轻地、几乎是虔敬地放在桌子中央,仿佛放下的不是一张牌,而是一段凝固了的时间。香烟的雾,茶的暖气,还有窗外斜照进来的、懒洋洋的日光,混在一起,将那桌上的牌局氤氲成一幅淡黄的旧画。我就在那画里,懵懂地认识了J、Q、K面上那些穿着异国服饰、表情永远严肃的古人,也第一次隐约感到,这五十四张纸片里,藏着一个缩微的、井然有序的小世界。
这个世界,自有其严酷的另一的另一面。待到年纪稍长,与同龄的伙伴们玩起“争上游”,那感觉便截然不同了。课间的十分钟,水泥乒乓球台就是我们的战场。那时的牌,是崭新的,硬挺挺的,带着一股油墨的冲鼻气味。甩牌时必要使出全身的力气,让那一声“啪”清脆响亮,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。在这里,“友情第一”是句空话,我们红着眼睛,较着劲,为一张“大王”能压住对方的“小王”而欢呼雀跃,也为一步失算而满盘皆输懊恼良久。小小的牌桌上,竟也上演着上演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。那些冰冷的规则,像铁一样硬,不容你撒娇,也不同情眼泪。它是我所接触到的,关于“胜负”与“规则”最初也最直接的教育。
后来读了些杂书,才晓得这小小的方寸之物,竟藏着如此深邃的玄机。那四种花色,像是人生的四种底色。那饱满而殷红的红桃,是心,是爱与激情,是胸膛里滚烫的热血;那黑色的、三叶草般的梅花,是幸运的象征,抑或是田埂间质朴的劳作?那形如盔顶的方片,闪着金属的冷光,是财富与权力的坚硬棱角;而那柄凛冽的黑色宝剑,是矛,是冲突,是生命中无法回避的决断与伤害。至于那超然于序列之外的“王”与“后”,更是平添了一重命运的诡谲。他们至高无上,却也要遵从摸牌的偶然;他们能主宰牌局的走向,自己的归属却又是一桩悬案。这哪里是牌,这分明是一面镜子,照见人世间的爱憎、得失、机运与无常。
想着这些,手里的牌也仿佛有了不同的分量。我将它们一张张在桌上铺开,排成扇面的形状。那些符号与数字,在灯下静默着,像一群等待上演的演员。我想起卡尔维诺说过,作品的意义在于它所能呈现的种种可能性。这一副牌,它的可能性便是无穷的。它可以是一场家庭聚会里温馨的背景音,可以是赌场中决定荣辱的残酷骰子,可以是魔术师指尖颠覆现实的幻梦,也可以是数学家笔下排列组合的冰冷模型。
我终究没有开始一局游戏。只是将牌重新收拢,妥帖地放回那只微微变形的纸盒里。窗外,夜色已浓,万籁俱寂。我忽然觉得,我所珍爱的,或许并非是玩牌本身,而是这洗牌、切牌之间,那一段可以被自己全然掌控的、安详而完整的时间。在这段时间里,我不是任何社会意义上的角色,我只是我自己,面对着五十四种可能,像一个君王,检阅着自己静默而忠诚的思想军队。
时间的河流,就这样在牌桌之上,无声而又不舍昼夜地,流过去了。而我们,都是这副古老纸牌里,一张张面目模糊,却又努力想讲出自己故事的,崭新的牌。
wepoker官网入口